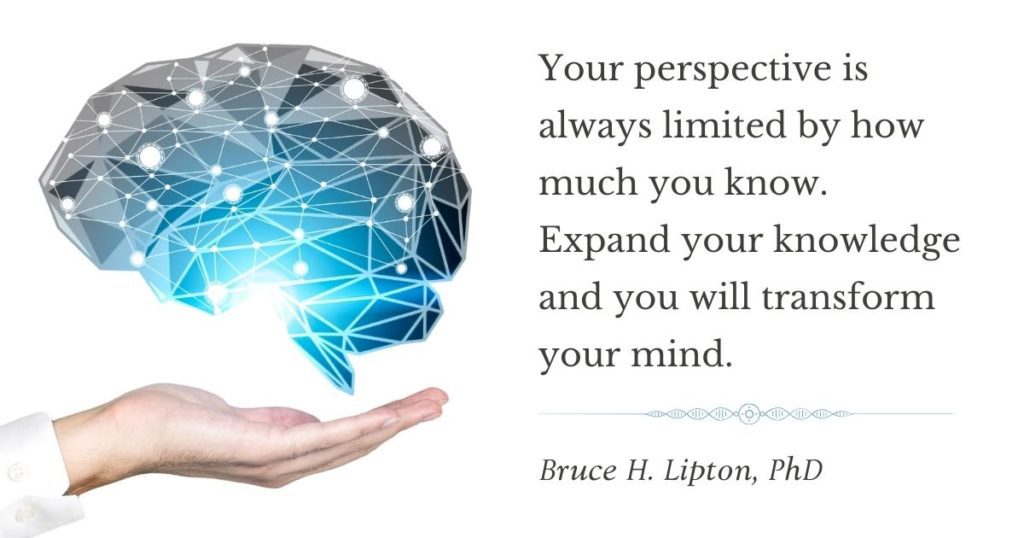
最初發表於 產前和圍產期心理學與健康雜誌,16(2),2001 年冬季
摘要:鑑於人類基因組計劃令人驚訝的結果,必須重新考慮先天后天的作用。 傳統生物學強調人類表達受基因控制,受自然影響。 由於 95% 的人口擁有“健康”基因,因此該人口的功能障礙可歸因於環境影響(後天培養)。 在子宮內開始的培育經驗提供了“習得的認知”。 與遺傳本能一起,這些感知構成了塑造生命的潛意識。 意識意識在六歲左右運作,獨立於潛意識運作。 有意識的頭腦可以觀察和批評行為錄音,但不能“強迫”潛意識的改變。
在生物醫學科學家中,經常引起爭議的一項長期爭論涉及自然與養育在生命發展中的作用[Lipton,1998a]。 那些與自然兩極分化的人將基因決定論的概念稱為負責“控制”生物體生理和行為特徵表達的機制。 遺傳決定論是指類似於遺傳編碼“計算機”程序的內部控制機制。 從概念上講,人們認為,選定的母本和父本基因的差異激活共同“下載”了個體的生理和行為特徵,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生物學命運。
相比之下,那些支持通過後天“控制”的人認為環境有助於“控制”生物表達。 養育者並沒有將生物命運歸因於基因控制,而是認為環境經驗在塑造個人生活特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哲學之間的極性僅僅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支持自然的人相信內部控制機制(基因),而支持培育機制的人則歸因於外部控制(環境)。
在定義育兒在人類發展中的作用方面,解決自然和養育爭議非常重要。 如果那些認可自然作為“控制”來源的人是正確的,那麼從概念上講,兒童的基本特徵和屬性在遺傳上是預定的。 推測是自我激活的基因將控制機體的結構和功能。 由於發育將由內在的基因進行編程和執行,因此父母的基本作用將是為成長中的胎兒或孩子提供營養和保護。
在這種模型中,偏離規範的發育特徵暗示該個體表達缺陷基因。 自然“控制”生物學的信念在人的生活發展中孕育了受害和不負責任的觀念。 “不要為這種情況而怪我,我是在我的基因中發現了它。 由於我無法控制自己的基因,因此我對後果不承擔任何責任。” 現代醫學認為,功能失調的個體具有缺陷的“機制”。 功能失常的“機制”目前正在用藥物治療,儘管製藥公司已經吹噓未來,基因工程將永久消除所有異常或不良特徵和行為。 因此,我們放棄了對生活的個人控制權,轉而使用製藥公司提供的“魔術子彈”。
在大量外行人和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支持下,另一種觀點擴展了父母在人類發展中的作用。 那些將養育作為生活的“控制”機制的人認為,父母對其後代的發育表達具有根本影響。 在一個受人控制的系統中,基因活性將動態鏈接到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 有些環境會增強兒童的潛能,而其他環境可能會導致功能障礙和疾病。 與博物學家所設想的固定命運機制相反,養育機制提供了通過調節或“控制”其環境來塑造其生物表達的機會。
回顧多年來的先天-後天爭議,很明顯,有時,對自然機制的支持勝過後天的概念,而在其他時候,情況恰恰相反。 自 1953 年 Watson 和 Crick 揭示 DNA 遺傳密碼以來,控制我們生理和行為的自我調節基因的概念已經戰勝了環境信號的感知影響。幾乎所有負面或有缺陷的人類特徵都代表了人類分子機制的機械故障。 到 1980 年代初,生物學家完全相信基因“控制”生物學。 人們進一步假設,完整的人類基因組圖將為科學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不僅可以“治愈”人類的所有疾病,還可以創造出莫扎特或另一個愛因斯坦。 由此產生的人類基因組計劃被設計為致力於破譯人類遺傳密碼的全球性努力。
基因的主要功能是作為生化藍圖,對蛋白質的複雜化學結構進行編碼,蛋白質是構建細胞的分子“部分”。 傳統觀點認為,構成我們身體的 70,000 到 90,000 種不同蛋白質中的每一種都由一個基因編碼。 除了蛋白質編碼基因,細胞還包含“控制”其他基因表達的調控基因。 調節基因大概協調了大量結構基因的活動,這些基因的行為共同貢獻了複雜的物理模式,為每個物種提供了其特定的解剖結構。 進一步推測其他調節基因控制諸如意識、情感和智力等特徵的表達。
在該項目啟動之前,科學家已經估計,人類的複雜性將需要一個超過100,000個基因的基因組(基因的總集合)。 這是基於保守的估計,在人類基因組中存儲了超過30,000個調節基因和超過70,000個蛋白質編碼基因。 今年,當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結果被報導時,結論本身就是“宇宙笑話”。 就在科學認為生命已經全部解決的時候,宇宙就拋出了一個生物曲線球。 在人類基因密碼測序的所有喧囂中,並陷入了光輝的技術壯舉中,我們並未關注結果的實際“含義”。 這些結果推翻了常規科學所擁護的基本核心信念。
Genome項目的宇宙笑話涉及到整個人類基因組僅由34,000個基因組成的事實[請參見Science 2001,291(5507)和Nature 2001,409(6822)]。 三分之二的預期和假定必需基因不存在! 當甚至沒有足夠的基因來僅編碼蛋白質的時候,我們如何解釋遺傳控制的人類的複雜性呢?
基因組的“失敗”證實了我們的期望,這表明我們對生物學“工作原理”的認識是基於錯誤的假設或信息。 我們對遺傳決定論概念的“信仰”顯然存在根本缺陷。 我們不能僅僅將生活特徵歸因於固有遺傳“編程”的結果。 基因組結果迫使我們重新考慮以下問題:“我們從哪裡獲得生物學上的複雜性?” 在評論人類基因組研究的令人驚訝的結果時,世界上最著名的遺傳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之一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2001)談到了這一複雜性問題:
“但是除非人類基因組包含許多對我們的計算機不透明的基因,否則很明顯,我們不會通過使用更多的基因來獲得比蠕蟲和植物毫無疑問的複雜性。
了解什麼使我們變得複雜 –我們龐大的行為方式,有意識的行動能力,出色的身體協調能力,對環境,學習,記憶的外部變化做出精確調整的變化……我需要繼續嗎? 仍然是未來的挑戰。 “ [巴爾的摩,2001年,重點是我的]。
當然,該項目結果最有趣的結果是,我們現在必鬚麵對巴爾的摩所暗示的“對未來的挑戰”。 如果不是基因,什麼將“控制”我們的生物學? 在基因組狂熱的背景下,對項目的重視使許多生物學家的出色工作蒙上了陰影,他們揭示了對有機“控制”機制的根本不同的理解。 在細胞科學的最前沿出現的一種認識是,環境,尤其是我們對環境的感知,直接控制著我們的行為和基因活性(Thaler,1994)。
常規生物學已經基於所謂的“中央教條”建立了自己的知識。 這種不可侵犯的信念聲稱,生物有機體中的信息流是從DNA到RNA,再到蛋白。 由於DNA(基因)是此信息流的最高層,因此科學採用了DNA的首要性概念,在這種情況下,“首要性”是第一個原因。 遺傳確定性的論據基於前提是DNA處於“控制”狀態。 但是,是嗎?
細胞的幾乎所有基因都存儲在其最大的細胞器細胞核中。 傳統科學認為細胞核代表“細胞的指揮中心”,這一概念基於基因“控制”(確定)細胞表達的假設(Vinson等,2000)。 作為細胞的“指揮中心”,暗示著細胞核相當於細胞的“大腦”。
如果大腦從任何活的有機體中取出,那麼該行為的必然結果就是有機體立即死亡。 然而,如果從細胞中取出細胞核,細胞不一定會死亡。 一些去核細胞可以在不擁有任何基因的情況下存活兩到幾個月。 去核細胞通常用作支持其他特殊細胞類型生長的“飼養層”。 在沒有細胞核的情況下,細胞維持新陳代謝、消化食物、排泄廢物、呼吸、在環境中移動,識別其他細胞、捕食者或毒素並做出適當的反應。 最終這些細胞會死亡,因為沒有它們的基因組,去核細胞無法替代生命功能所需的磨損或有缺陷的蛋白質。
細胞在沒有基因的情況下維持成功和完整的生命這一事實表明,基因不是細胞的“大腦”。 基因不能“控制”生物學的主要原因是它們不是自我湧現的(Nijhout,1990)。 這意味著基因不能自我實現,它們在化學上無法打開或關閉自己。 基因表達受通過表觀遺傳機制起作用的環境信號的調節控制(Nijhout,1990,Symer 和 Bender,2001)。
然而,基因是生命正常表達的基礎。 基因而不是充當“對照”的能力,而是代表製造複雜蛋白質所需的分子藍圖,複雜蛋白質提供細胞的結構和功能。 基因程序中的缺陷,突變可能會嚴重損害擁有它們的人的生活質量。 重要的是要注意,不到5%的人口的生命受到缺陷基因的影響。 這些人無論是在出生時出現還是在以後的生活中都表現出遺傳繁殖的先天缺陷。
該數據的意義在於,超過95%的人口進入了這個擁有完整基因組的世界,該基因組編碼著健康而健康的生活。 儘管科學致力於通過研究具有缺陷基因的人群的%5來評估基因的作用,但對於為何擁有合適基因組的大多數人群會出現功能障礙和疾病,這方面並沒有取得太大進展。 我們根本不能將其現實“怪罪”到基因(自然)上。
關於“控制”生物學從DNA轉移到細胞膜的科學關注(Lipton等,1991,1992,1998b,1999)。 在電池的經濟性方面,膜相當於我們的“皮膚”。 膜在不斷變化的環境(非自身)和封閉的細胞質受控環境(自身)之間提供了接口。 胚胎的“皮膚”(外胚層)為人體提供了兩個器官系統:被膜和神經系統。 在細胞中,這兩個功能整合在包裹細胞質的簡單層中。
細胞膜中的蛋白質分子將內部生理機制的要求與現有環境的緊急情況聯繫在一起(Lipton,1999)。 這些膜“對照”分子由由受體蛋白和效應蛋白組成的couple聯組成。 蛋白質受體以與我們的受體(例如,眼睛,耳朵,鼻子,味道等)讀取環境相同的方式識別環境信號(信息)。 特定受體蛋白在收到可識別的環境信號(刺激)後被化學“激活”。 在其激活狀態下,受體蛋白與特定的效應蛋白偶聯,進而激活特定的效應蛋白。 “激活的”效應蛋白選擇性地“控制”細胞的生物學,從而協調對起始環境信號的反應。
受體效應蛋白複合物充當“開關”,將有機體的功能整合到其環境中。 開關的接收器組件提供“環境意識”,而效應器組件響應於該意識而產生“物理感覺”。 根據結構和功能的定義,受體效應器開關代表感知的分子單元,被定義為“通過物理感覺感知環境”。 感知蛋白複合物“控制”細胞行為,調節基因表達,並已牽涉遺傳密碼的重寫(Lipton,1999)。
每個細胞天生都是聰明的,因為它通常具有遺傳“藍圖”,可以創建所有必需的感知複合體,使其能夠在正常的環境環境中生存和繁衍。 在XNUMX億年的進化過程中,細胞已獲得併積累了編碼這些知覺蛋白質複合物的DNA。 知覺編碼基因存儲在細胞核中,並在細胞分裂前複製,從而為每個子細胞提供一組維持生命的知覺複合體。
但是,環境不是靜態的。 環境的變化使居住在這些環境中的生物體產生了對“新”感知的需求。 現在很明顯,細胞通過與新的環境刺激物相互作用而產生新的感知複合物。 利用一組新發現的基因(統稱為“基因工程基因”),細胞能夠在代表細胞學習和記憶的過程中產生新的感知蛋白(Cairns,1988年,Thaler 1994年,Appenzeller,1999年,Chicurel,2001年) 。
這種進化上先進的基因寫入機制使我們的免疫細胞能夠通過創造救生抗體來應對外源抗原(Joyce,1997; Wedemayer等,1997)。抗原。 作為蛋白質,抗體需要一個基因(“藍圖”)進行組裝。 有趣的是,在細胞暴露於抗原之前,不存在源自免疫反應的專門定制的抗體基因。 從最初接觸抗原到出現特異性抗體大約需要三天的免疫應答,導致“學習”一種新的感知蛋白(抗體),其DNA的“藍圖”(“記憶”)可以被識別。通過遺傳途徑傳給所有子細胞。
在建立生命感知過程中,細胞必須將信號接收受體與效應蛋白偶聯,以“控制”適當的行為反應。 感知的特徵可以通過環境刺激引起的反應類型來評分。 積極的看法會產生生長反應,而消極的看法會激活細胞的保護反應(Lipton,1998b,1999)。
儘管感知蛋白是通過分子遺傳機制製造的,但是感知過程的激活是由環境信號“控制”或引發的。 細胞的表達主要是由其對環境的感知而非其遺傳密碼所塑造的,這一事實強調了營養在生物控制中的作用。 最近對乾細胞的研究強調了環境的控制性影響(Vogel,2000)。 在成體的不同器官和組織中發現的干細胞與胚胎細胞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未分化,儘管它們具有表達多種成熟細胞類型的潛力。 幹細胞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 幹細胞的分化基於細胞所處的環境。例如,可以創建三種不同的組織培養環境。 如果將乾細胞放在第一培養物中,它可能會變成骨細胞。 如果將相同的干細胞放入培養XNUMX中,它將變成神經細胞,或者如果將其放入培養皿XNUMX中,則該細胞會像肝細胞一樣成熟。 細胞的命運是由其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控制”的,而不是由獨立的遺傳程序控制的。
雖然每個細胞都能夠作為一個自由生活的實體運行,但在進化後期細胞開始組裝成互動社區。 細胞的社會組織源於提高生存率的進化驅動。 一個有機體擁有的“意識”越多,它的生存能力就越強。 考慮單個單元格具有 X 量的感知。 那麼 25 個細胞的集落將具有 25X 的集體意識。 由於社區中的每個細胞都有機會與群體中的其他人分享意識,因此每個細胞都有效地擁有 25X 的集體意識。 具有 1X 意識的細胞或具有 25X 意識的細胞哪個更有生存能力? 大自然傾向於將細胞組裝成群落,以此作為擴大意識的手段。
從單細胞生命形式到多細胞(公共)生命形式的進化過渡代表了生物圈創建過程中的知識和技術深遠的高潮。 在單細胞原生動物世界中,每個細胞都是與生俱來的智能,獨立的存在,並根據自身對環境的感知調整其生物學。 但是,當細胞結合在一起形成多細胞“社區”時,要求細胞建立復雜的社交關係。 在社區內,單個細胞不能獨立運行,否則社區將不復存在。 根據定義,社區成員必須遵循單一的“集體”聲音。 控制社區表達的“集體”聲音代表了該組中每個單元的所有感知的總和。
原始的細胞群落由數十到數百個細胞組成。 生活在社區中的進化優勢很快導致了由數百萬,數十億甚至數万億個社交互動單細胞組成的組織。 為了在如此高的密度下生存,細胞進化出的驚人技術導致了高度結構化的環境,這將使人類工程師的思維和想像力陷入僵局。 在這些環境中,小區社區將工作負載細分為多個小區,從而創建了數百種專門的小區類型。 創建這些互動社區和分化細胞的結構計劃被寫入社區中每個細胞的基因組中。
儘管每個單獨的細胞都具有微觀尺寸,但多細胞群落的大小可能從幾乎看不到的比例到整體的比例不等。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我們沒有觀察到單個細胞,但我們確實認識到細胞群落獲得的不同結構形式。 我們將這些宏觀結構化社區視為動植物,其中包括我們自己。 雖然您可能會將自己視為一個整體,但實際上,您是大約50萬億個單個單元的社區的總和。
通過組成單元之間的勞動力細分,可以提高此類大型社區的效率。 細胞學專業技術使細胞能夠形成人體的特定組織和器官。 在較大的生物中,只有一小部分的細胞在感知社區的外部環境中起作用。 一群專門的“知覺細胞”形成神經系統的組織和器官。 神經系統的功能是感知環境並協調細胞群落對撞擊環境刺激的生物學反應。
像它們所組成的細胞一樣,多細胞生物在遺傳上具有基本的蛋白質感知複合體,使該生物能夠在其環境中有效生存。 基因編程的知覺被稱為本能。 與細胞相似,生物也能夠與環境相互作用並創造新的感知途徑。 此過程提供了學習的行為。
隨著一棵進化樹從更原始的進化為更先進的多細胞生物,從主要使用遺傳程序化知覺(本能)到使用學習行為發生了深刻的轉變。 原始生物主要依賴於本能來獲得更大比例的行為。 在高等生物特別是人類中,大腦進化為建立龐大的學習知覺數據庫提供了絕佳機會,從而減少了對本能的依賴。 人類被賦予了豐富的遺傳繁殖的生命本能。 它們中的大多數對我們來說並不明顯,因為它們在我們的意識水平以下運作,提供了細胞,組織和器官的功能和維持功能。 但是,一些基本的本能會產生明顯且可觀察的行為。 例如,新生兒的乳頭反應,或手指在火焰中燃燒時手的縮回。
“人類比其他物種更依賴學習來生存。 例如,我們沒有本能自動保護我們並找到食物和庇護所的直覺。” (Schultz and Lavenda,1987)儘管本能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但我們的博學見識更為重要,尤其是考慮到它們可以超越基因編程的本能這一事實。 由於知覺指導基因活動並參與行為,因此我們獲得的學習知覺有助於“控制”我們生活的生理和行為特徵。 我們的直覺和所學知覺的總和共同構成了潛意識,這反過來又成為我們細胞“同意”遵循的“集體”聲音的來源。
儘管我們擁有天生的感知力(本能),但我們只是在神經系統開始運作時才開始獲得學習的感知力。 直到最近,傳統思想仍認為人腦要在出生後的某個時候才能發揮功能,因為直到那時人類的許多結構都尚未完全分化(發育)。 然而,托馬斯·弗尼(Thomas Verny,1981)和戴維·張伯倫(David Chamberlain,1988)等人的開創性工作使這一假設無效。這些工作揭示了胎兒神經系統所表現出的巨大的感官和學習能力。
這種理解的意義在於,胎兒所經歷的感知將對其胎兒的生理和發育產生深遠的影響。 本質上,胎兒的感受與母親的感受相同。 胎兒的血液通過胎盤與母親的血液直接接觸。 血液是結締組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通過它可以通過協調人體系統功能的大多數組織因子(例如激素,生長因子,細胞因子)。 當母親回應對環境的感知時,她的神經系統激活了行為協調信號向血液中的釋放。 這些調節信號控制著她進行所需的行為反應所需的組織和器官的功能,甚至是基因活性。
例如,如果母親在環境壓力下,她將激活她的腎上腺系統,這是一種為戰鬥或逃跑提供保護的系統。 這些釋放到血液中的壓力荷爾蒙可以使身體做好保護反應的準備。 在此過程中,內臟血管收縮,迫使血液滋養提供保護的外周肌肉和骨骼。 戰鬥或逃跑反應取決於反射行為(後腦),而不是意識推理(前腦)。 為了促進這一過程,壓力荷爾蒙會收縮前腦的血管,迫使更多的血液流向後腦,以支持反射行為功能。 在應激反應過程中,腸道和前腦的血管收縮分別抑制了生長和有意識的推理(智力)。
現在已經認識到,母親血液中的營養成分,壓力信號和其他協調因素與之一起穿過胎盤進入胎兒系統(Christensen 2000)。 這些母體調節信號一旦進入胎兒血流,便會像影響母親一樣影響胎兒中的靶標系統。 胎兒同時經歷母親對環境刺激的感知。 在壓力環境中,胎兒血液優先流向肌肉和後腦,同時又縮短了流向內臟和前腦的流量。 胎兒組織和器官的發育與它們接收的血液量成正比。 因此,患有慢性壓力的母親將深刻改變孩子的生理系統的發育,從而為孩子的成長和提供保護。
個人獲得的學識開始出現在子宮內,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組外向的學習知覺“控制”了我們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大自然創造了促進這種早期學習過程的機制。 在遇到新的環境刺激時,新生兒被編程為首先觀察母親或父親如何響應該信號。 嬰兒特別擅長解釋父母的面部特徵,以區別新刺激的積極或消極性質。 當嬰兒遇到新的環境特徵時,通常首先要關注父母的表情,以學習如何應對。 一旦識別出新的環境特徵,便會加上適當的行為響應。 耦合的輸入(環境刺激)和輸出(行為響應)程序作為學習的知覺存儲在潛意識中。 如果刺激再次出現,則由潛意識感知編碼的“程序化”行為將立即參與。 行為基於簡單的刺激響應機制。
從簡單的物體到復雜的社會互動,都會產生外向型的學習感知。 集體地,這些學到的看法有助於個人的培養。 父母對孩子的潛意識行為進行“編程”可以使孩子符合社區的“集體”聲音或信念。
除了外向型感知,人類還獲得內向型感知,這向我們提供了關於“自我身份”的信念。 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我們學會了像別人看到我們一樣看待自己。 如果父母為孩子提供正面或負面的自我形象,則該感知會記錄在孩子的潛意識中。 自我獲得的圖像成為潛意識的“集體”聲音,它塑造了我們的生理(例如健康特徵,體重)和行為。 儘管每個單元都有天生的智慧,但根據公共協議,它會效忠於集體聲音,即使該聲音參與了自我毀滅性活動。 例如,如果讓孩子意識到自己可以成功,那麼它將不斷努力做到這一點。 但是,如果給同一個孩子以“不夠好”的信念,那麼身體就必須遵守這種看法,甚至在必要時通過自我破壞來阻止成功。
人類生物學非常依賴於所學知覺,因此進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鼓勵快速學習的機制也就不足為奇了。 可以使用腦電圖(EEG)以電子方式測量大腦活動和意識狀態。 有四種基本的意識狀態,以大腦中電磁活動的頻率來區分。 個人在這些EEG狀態中度過的時間與兒童發育期間表達的模式順序有關(Laibow,1999)。
最低活動水平的DELTA波(0.5-4 Hz)主要在出生和兩歲之間表達。 當一個人處於DELTA狀態時,他們處於無意識(睡眠)狀態。 在兩歲到六歲之間,孩子開始將更多的時間花在較高水平的腦電活動中,稱為THETA(4-8 Hz)。THETA活動是我們剛出生一半時所經歷的狀態。睡著了,半睡著了。 孩子們玩耍時會處於這種極富想像力的狀態,用舊掃帚上的泥漿或英勇的馬匹製成美味的餡餅。
六歲左右的孩子開始優先表達更高水平的腦電活動,稱為ALPHA波。 ALPHA(8-12 HZ)與鎮定狀態有關。 在大約12歲時,孩子的腦電圖譜可以表達持續的BETA(12-35 HZ)波,這是腦活動的最高水平,被稱為“主動或專注的意識”。
這種發育譜的意義在於,一個人通常要到五歲以後才能保持主動意識(ALPHA活動)。 在出生之前和生命的頭五年,嬰兒主要處於DELTA和THETA狀態,這代表著催眠狀態。 為了催眠一個人,有必要將他們的大腦功能降低到這些活動水平。 因此,孩子在生命的最初五年中基本上處於催眠狀態。 在這段時間裡,它甚至在沒有意識歧視的好處或乾擾的情況下,減輕了對生物控制的認識。 在這個發展階段,孩子的潛能被“編程”到潛意識中。
所學知覺被“硬連線”作為潛意識中的突觸途徑,本質上代表了我們所認識的大腦。 意識在大約六年的生命中以ALPHA波的形式在功能上自我表達,與大腦的最新成員即額葉皮層有關。 人類意識的特徵在於對“自我”的意識。 當我們大多數的感覺(例如,眼睛,耳朵和鼻子)觀察外部世界時,意識就像是一種“感覺”,它觀察了其自身細胞群落的內部運作方式。 意識可以感覺到身體產生的感覺和情感,並可以訪問包含我們的感知庫的存儲數據庫。
要了解潛意識和意識之間的區別,請考慮這種指導性的關係:潛意識代表大腦的硬盤(ROM),而潛意識相當於“桌面”(RAM)。 就像硬盤一樣,潛意識可以存儲大量難以想像的感知數據。 可以將其編程為“在線”,這意味著傳入的信號直接進入數據庫並進行處理,而無需有意識的干預。
當意識演變為功能狀態時,關於生命的大多數基本觀念已被編程到硬盤驅動器中。 意識可以訪問該數據庫並開放供人們回顧以前學到的感知,例如行為腳本。 這與從硬盤驅動器打開文檔到桌面一樣。 在意識中,我們有能力查看腳本並根據需要編輯程序,就像在計算機上打開文檔一樣。 然而,編輯過程絕不會改變原始意識,而這種原始意識仍然牢牢地存在於潛意識中。 意識引起的大喊大叫或哄哄都不會改變潛意識程序。 由於某種原因,我們認為潛意識中有一個實體可以傾聽並回應我們的思想。 在現實中,潛意識是一個冷酷,毫無感情的存儲程序數據庫。 它的功能嚴格涉及讀取環境信號和參與硬接線行為程序,不問任何問題,不做任何判斷。
通過純粹的意志和意圖,意識可以企圖超越潛意識的磁帶。 通常,這些努力會遇到不同程度的抵抗,因為細胞必須遵守潛意識程序。 在某些情況下,有意識的意志力和下意識的程序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導致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 例如,考慮一下澳大利亞音樂會鋼琴家戴維·赫爾弗戈特(David Helfgott)的命運。 大衛是由父親(大屠殺的倖存者)編程的,他沒有成功,因為成功會使他脆弱,因為他會在別人中脫穎而出。 儘管他父親的編程無情,但大衛還是有意識地意識到自己是世界一流的鋼琴家。 為了證明自己,赫爾弗戈特特意選擇了最難的鋼琴作品之一,拉赫瑪尼諾夫(Rachmaninoff)創作的作品來參加全國比賽。 正如電影所揭示的那樣,在他驚人的表演的最後階段,他的有意識的成功意願與潛意識的程序失敗之間發生了重大衝突。 當他成功彈完最後一個音符時,他昏了過去,覺醒後他變得不可挽回地瘋狂。 他的意識將發揮力量的事實迫使他的身體機制違背了編程的“集體”聲音,導致神經系統崩潰。
我們通常在生活中遇到的衝突通常與我們試圖“強迫”改變潛意識程序的努力有關。 但是,通過各種新的能量心理學方法(例如Psych-K,EMDR,Avatar等),可以評估潛意識的內容,並使用特定的協議,意識可以促進對核心信念的快速“重新編程”。